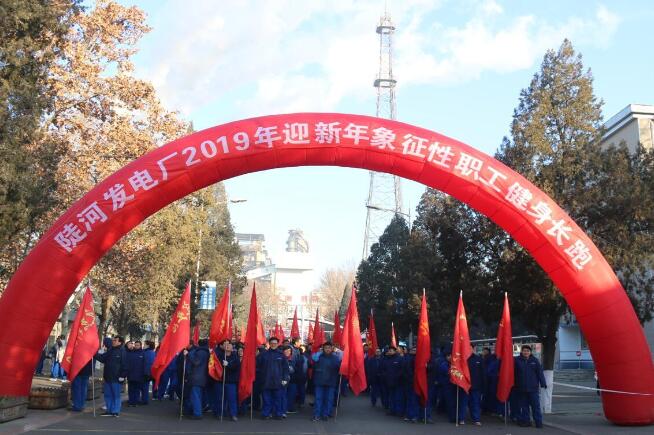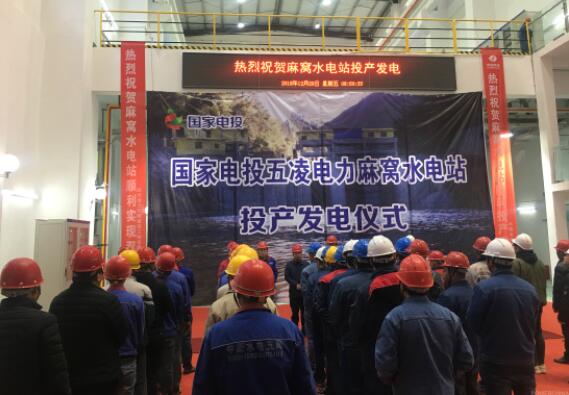在儿时的记忆中,外婆是最亲的人。
外婆娘家是筑金坝的,嫁到五羊坪来,生育了四男二女,个个有出息。然后守在五羊坪,像老母鸡一心一意抚育我们这些小鸡崽。
二舅因为地下党问题牵连遭受冤屈,一直窝在老家劳动改造。二舅妈常年在外地教书,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二舅家六个子女几乎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加上我家姐妹和衡阳的表姐妹,按现在的说法外婆家是地地道道的托儿所,更是舅舅姨妈和我爸妈的根据地大后方。
抚育这么大一群小孩子,要煮饭洗衣喂猪操持家务,外婆的辛苦可想而知,却从没见她发过脾气,我们见到的永远是外婆慈祥的笑脸。
每到饭点,外婆在门前地坪里亮开嗓子一身呼唤:恰饭罗!我们这群小鸡崽就纷纷从各角落钻出来奔向饭桌。如果喊得两句没回音,外婆就“丽伢、卫伢。。。。。。”的依次点名,拖长音调唱歌似的在八元堂上空回响。
夏天洗澡最热闹。除了表哥自己在塘里“打泡求”,表姐躲在房里,我们这些小屁孩站在地坪里一溜光屁股排队,外婆用大木澡盆挨个儿洗我们这些泥猴,洗完一个换盆水,流水线似的,洗干净了啪嗒啪嗒圾拉着木拖鞋自己穿裤衩。
“晚饭晚饭,点灯恰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小鸡崽们变成了小猪崽,南瓜汤锅巴粥吸溜吸溜灌个饱。然后吆三喝四抬竹床扛椿櫈到晒谷坪里歇凉。
外婆洗刷完锅碗,洗干净全家的衣服,才有空自己洗澡。然后把每一张床蚊帐里躲的蚊子用大蒲扇赶出来,放下蚊帐扎紧,拖着疲惫的脚步到晒谷坪里接替外公,给一溜儿躺在竹床上瞪着眼睛数星星的我们扇风赶蚊子。
因为外公会手艺,二舅妈当老师能拿工资,我们家是比较殷实的,油啊盐啊几乎没缺过。
有的人家常年吃红锅子(炒菜时锅里不放油),实在熬不住了就派小孩子来借油,一般是一酒盅或一汤匙,小心翼翼端回家,用小块布条轻轻在油里蘸一下,在锅里画个圈,算是炒菜放了油。
外婆经常叫读书的大表姐把借油的帐用粉笔头写在火柜(橱柜)侧壁上,收了油菜或捡了野茶籽的时节,人家会把借的油还过来,柜壁上的粉笔字自然就没有了——外婆会把那些贫苦人家还不起的账目也一并抹掉。
我们这些小鸡崽崽翅膀刚刚开始长出羽毛,就一个接一个飞出去了。
离别的时候,哭得最伤心的是外婆,嚎得惊天动地的是舍不得离开外婆的我,二舅红着眼圈连骗带哄硬生生的把我从外婆紧紧的怀抱里拉出来,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拖着我上船“搭漂”,外婆吃力的扭着小脚哭喊着往河边赶,眼睁睁的看着在船上同样哭喊的我慢慢消失在河的远方。
五十多年啦,外婆在高高的河岸上挥手哭喊的身影一直深深的印在脑海里。

主办单位:亚新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 网站运营:北京中电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400-007-1585
项目合作:400-007-1585 投稿:63413737 传真:010-58689040 投稿邮箱:yaoguisheng@chinapower.com.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京ICP证140522号 京ICP备14013100号 京公安备110106020101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