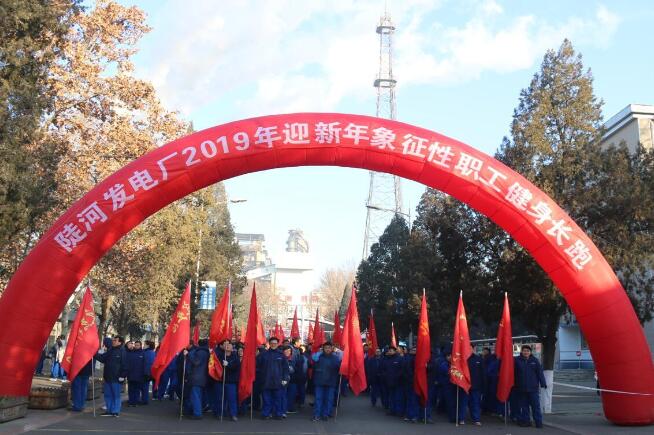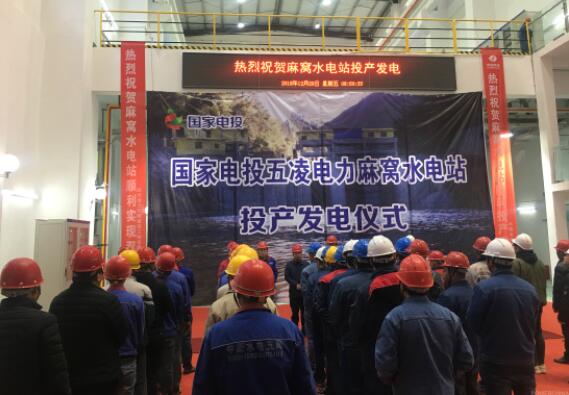草药的功效是肯定的。
画水或者是一种虔诚同时也增添了神秘感。
农民常年在太阳下劳作免不了上火,农妇终日在厨房忙碌煮饭炒菜熬猪食烟熏火燎眼睛也好不到哪里去,乡下人的眼疾大都是“火眼”,以清凉解热之法应可缓解。但我的一位对民间医术极感兴趣的朋友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外公治疗眼疾的办法必有奥秘,为我没有学得外公的真谛而大为遗憾。
其实真正的遗憾还在于外公的民间医术没有传给二舅的家人。或许这其中有苦衷——治疗眼疾要念咒语要画水,属于封建迷信。顶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二舅哪敢让子女学这东西哦
给人治好了病痛,朴素的乡下人自然是要来酬谢的。提二三十个鸡蛋或者捉只鸡或者割二斤肉上门来,也有河里捕的鱼和山里打的野物,然后是千恩万谢。外公忙着递上水烟袋,外婆“哐哐哐”的打擂茶,继而下厨做饭,提来的礼物立马上了饭桌,几杯米酒下肚就海阔天空神聊。这场景是我们这群小家伙最喜欢的,因为可以趁机会打打牙祭。
说到外公的医术,其实最受惠的是我。
我出生后,母亲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抚养,把我寄养在奶妈家,报酬是每年两担干谷(那年头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忙过一段时间后,母亲抽空来看望我,正巧撞见奶妈往我嘴里塞硬饭团。当时我好像只有几个月,邻居说奶妈根本没奶水,就是喂的米饭团。母亲气急,抱着我回了娘家,哭哭啼啼交到外婆手里。我严重缺乏营养,身体极度虚弱,衰弱的细脖子撑不住硕大的脑袋,软软的耷拉在肩膀上。外公叹了口气,说只怕难得养活。
嘴上不敢打包票,外公外婆还是下决心要养活我。放现在,恐怕是要进ICU了的,但那是五十年代初啊,婴幼儿成活率极低,小孩子就像小猫小狗。
找不到奶妈,外婆就用浓浓的米汤喂,硬是把我从阎王爷那儿抢回来。几个月后,外公每天早上跑三四里路过河到栗山河买两毛钱瘦肉(别笑,那年头猪肉只有六七毛钱一斤)剁碎了,用芡实薏米等其他中药材一起蒸烂,兹补我那虚弱的脾胃。快两岁了就想方设法哄我吃肥肉(我一沾肥肉就反胃),张开嘴,夹一筷腌菜放舌头上,然后放一丁点肥肉,再盖些腌菜,闭上眼睛使劲嚼。
如此精心调养,我终于慢慢好了起来。
后来听说,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子被外公外婆救活的。
不过,我还是很怕外公,他太严厉,在家人面前不苟言笑。尤其是管教小孩子,规矩极严。
在饭桌吃饭时左手一定要捧着碗;如若端着饭碗,大拇指必得扣紧碗沿,绝不许手掌托碗底,说那是“叫花子碗”,其实是怕端不稳打碎了。一碗菜摆在桌上,筷子伸过去只能夹自己这一边的;夹了菜直接送进嘴里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先放到自己饭碗里;假若筷子在菜碗里翻搅那就犯了大忌。稍有不慎,头上就会挨一筷子头,因而每次吃饭都战战兢兢。
最高兴有客人来,不但有肉吃,还可以不上桌,几个小家伙在外婆带领下和女人们在灶台边吃饭,哪怕一点点肉沫沫都会被小家伙们抢光。
外公做事很严谨,睡觉前必定到猪栏鸡埘巡视一遍,所有的门窗栓紧,灶里火塘里的火子拍严实,灶口的柴清扫干净,凳子椅子等所有杂物统统靠墙边。祖屋传下来这么多年没有火灾,应该是代代谨慎的结果。
外公表面严厉,内心其实是很文艺的,思想很开放。裁缝手艺不错,对乡邻极和善,方圆一二十里以至对河的株木潭都有极好的口碑。因为有手艺,不用下田劳作,种菜却是一把好手,菜园子常年受邻里羡慕。
春暖花开时节,田野一派生气勃勃。阳光普照,南风习习,似乎能听到万物拔节生长的声音。细伢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插田就是盛大的节日,家家都把腊鱼腊肉菜蔬白米饭摆到田头,祭祀的猪脑壳也供在田垄上。香烛缭绕,火铳轰轰。族长一声号令,男人女人通通下田插秧。外公则高高坐在凳子上,一边敲鼓一边放开喉咙唱歌,大约是祈祷风调雨顺好收成,唱到高兴时男男女女都直起腰来打和声。
后来听说外公唱的其实就是大栗港原生态的“胡呐喊”,声音很高很亮,好远都听得到。
如今不用弯腰插田,那“插田歌”大概也没人会唱了,据说“胡呐喊”也频临失传。
大年初一,女人们是不必下厨的,外公亲自做饭,说是女人们辛苦了一年,开年第一天歇气。正月十五也是外公做饭,让女人们疯玩。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最高兴,不光是有肉吃有新衣服新鞋子穿有压岁钱,主要的是那些天外公不会骂人。

主办单位:亚新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 网站运营:北京中电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400-007-1585
项目合作:400-007-1585 投稿:63413737 传真:010-58689040 投稿邮箱:yaoguisheng@chinapower.com.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京ICP证140522号 京ICP备14013100号 京公安备110106020101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