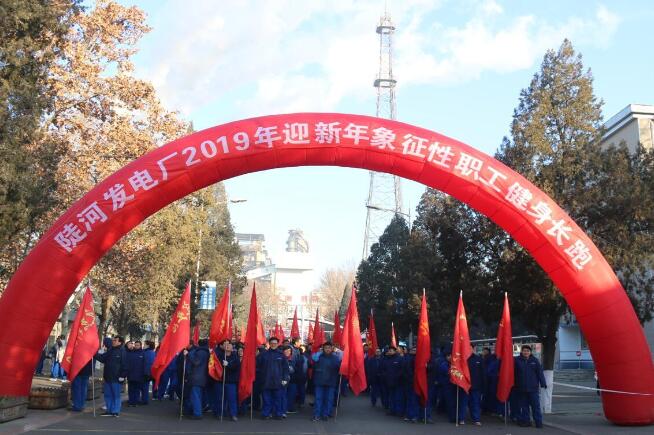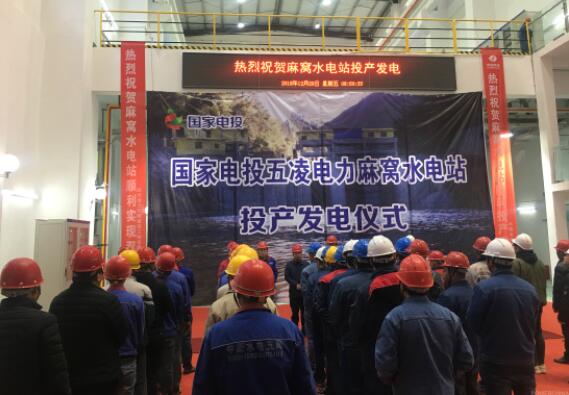五羊坪在资水南岸,东距桃江县城 三十多公里,是我外婆家。
资水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下来,冲破雪峰山脉和衡山山脉的夹击,跌跌撞撞一路流经宝庆、新化、安化、桃江、益阳,然后分别从甘溪港和临资口注入南洞庭湖。落差大水流湍急,山岚耸立峰回路转,河道弯弯曲曲。河流冲刷的地方形成潭,潭的对面则淤积成坪,这大约是五羊坪的来历。
五羊坪的上游是武潭,下游是大栗港,河对面是株木潭。河岸两边有曹家坪田家坪刘家坪。五羊坪那地方几乎都姓“熊”,却不叫熊家坪,我想这其中是必有故事的,因为下游三四里的栗山河也有个地方叫毛羊坪。
一、那屋
外婆家是一栋很大的祖屋,叫“八元堂”,坐北朝南的凹型结构,全部是木头造的,没有一块砖头。当然,屋顶盖的是瓦,也没用茅草。记忆最深的是每道门槛都很高,小时候翻过门槛很费劲。
为何叫八元堂?说是外公的八兄弟,一大家子住在一块。从房屋结构的走向和新旧可以看出,祖屋也是一代一代扩建开来的。
祖屋的正面是外公家祖宗的祠堂,供奉着诸多牌位。逢年过节,熊家的男丁一大早都要到祠堂祭拜祖宗,小孩子也跟在大人身后作揖磕头,女眷却不得跨入祠堂一步。
平常时节,祠堂的门是开着的,这里也是男人们的社交场所,尤其是下雨不能干农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家伙更喜欢凑热闹,成群结伙的在祠堂里打打闹闹,在搁于长凳上的几副“千年屋”(空棺材)之间捉迷藏。
冬天农闲阴雨下雪,青壮男丁就聚集在祠堂里习武,刀枪棍棒叉耍得寒光闪闪,锄头扁担长凳舞的呼呼生风。
若出得几天太阳,祖屋前地坪晒干了,男丁们就会举着长龙在地坪里吆喝喧天,锣鼓敲得震天响,因为每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时龙灯都要比赛的。
那场合每每是火流星开路,铁水流星绚丽的划破夜空,精壮小伙打着赤膊,龙头喷着火一路呼啸翻滚而来,鞭炮劈哩啪啦,火铳通通作响,绿莲船花蚌壳俏艄公踩高跷三棒鼓莲花落地花鼓胡呐喊应有尽有。
小孩子人手一盏纸扎的红灯笼,里面点着蜡烛,用竹棍儿挑了,提在手里相互炫耀,在大人们的的腋下胯间钻来窜去。
姑娘媳妇都是花花绿绿的新棉袄,搭肩挽手嘻嘻哈哈笑得直不起腰,也难怪,一年到头她们难得这么放肆一回。
队伍在八元堂闹腾一通就到邻近的祠堂里去闹,人家的队伍也会到八元堂来,反正都是熊家的祠堂。如果两支队伍撞上了,一场较劲是必然的,锣鼓狠劲的敲,龙狮拼命的舞,唱戏的扯着嗓子喊。那场合是一年中最热闹的。
外婆家在祖屋的南侧,东南侧是满妈家,东北侧是八妈家,最南侧是外公的第六个哥哥,据说年轻时放簰被土匪刺了一刀,身体不好,终身未娶,孤鳏一生。我母亲年幼时过继给这位叔外公,也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她年纪轻轻就干革命去了,后来嫁到三堂街,再后来去了益阳当老师。当然叔外公病重以至过世,母亲还是尽了当女儿的孝心。
祠堂的西侧好像是五妈家,再往西就有点搞不清了,只知道紧靠这凹型结构又有一栋H型老屋,也是住的熊姓人家,却不是外公这一支的族人,印象较深的是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而靠捞小鱼虾维持生计的的戴云。
我们这头的老屋虽然拥挤着住了好几家,但每家都有走廊隔开,且每家都有独立的堂屋灶屋和几间睡房,也都有各自的猪栏屋柴房茅房和鸡埘。
各家之间通向大厅,大厅竖着一架巨大的板梯,可以通到各家的阁楼上,搁些不常用的大型用具和工具。五四年涨大水,资江洪水漫出来淹掉了五羊坪,八元堂的老老小小全都躲到了阁楼上,因而这架板梯得以保留。
还有一座硕大无比的谷仓,挂着牛鼻子铜锁。一直搞不懂这谷仓是干什么用的,生产队的谷仓在队屋里,各家分的谷子堆在自家的杂屋里,那谷仓大部分时间是空荡荡的,有时候却存了些谷子在里面。或许,这大谷仓是外公的爷爷留下来的吧?仓里的谷子是囤起来灾年时共同度荒的吧?
人民公社时,八元堂这块地方被划为八一生产队。生产队的牛栏在祖屋的西南侧。大食堂在H型屋里,那是每天最热火的地方。晒谷坪和队屋在东南侧,与祖屋隔着一条小水沟。夏天的夜晚,熏起一堆晒干了的辣蓼子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扛着或抬着竹床到晒谷坪纳凉。我们这些小孩子先是疯玩,玩累了就静静地围在老人身边听故事。讲妖魔鬼怪时听得害怕,不由自主的往人堆中间挤。听着听着进入了梦乡,外公或外婆就给我们轻轻的摇蒲扇,半夜时分再把我们背回床上。
那床都是雕花架子床,床前是放鞋子的踏板。架子床永远都挂着手工织的又厚又密的麻布蚊帐,蚊帐里像蒸笼,一身的汗跟睡在水里似的。这时候,外婆又会拿着蒲扇给我扇风,于是迷迷瞪瞪睡得像小猪。外婆半坐半躺依靠着床架打瞌睡,手里的蒲扇有气无力有一下没一下的摇晃一通宵。
无论冬夏,雕花床永远铺着厚厚的稻草,乡下管它叫“床铺草”,松松的软软的,散发一股沁人心肺的清香。床铺草每年都会换新的,换下来的旧床铺草是不能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烧,只晓得这是禁忌。
冬天的晚上,全家都围在堂屋的火塘边。
男人一边抽烟一边和串门的邻居聊天,往一米多长的竹竿铜头烟袋里塞满金黄色的旱烟丝,伸到火塘里点燃,把黄灿灿的铜烟嘴含在胡子拉渣的嘴巴里美美的吸上一口,递给别人之前还不忘用粗糙的大手掌把铜烟嘴抹一把。
女人低着头就着火光纳鞋底或坐在侧边纺纱。旧布为里新布为面,用米汤一层层糊好晒干,剪成鞋底模样,用粗麻线密密实实的纳满。永远都记得纳鞋底的动作——鞋底夹在鞋夹板上,双脚踩住夹板底部,先用锥子在鞋底上钻个孔,两根粗针引着麻线对穿过来,再咬着牙使劲把麻线绷紧。一锥一孔,一孔两线,而且每次钻孔之前都要把锥尖在头发里插几下。
纺纱时右脚踏住纺车底板,右手顺时针摇动纺车,左手捏住棉条,捻出细细的纱线,舒展手臂向后方尽力延伸,然后缩回来,长长的纱线就会自动缠绕到线轴上,如此往复不已。
除非有客人来,大多时候烤火不会太久,因为废不起柴火。这时候,纺车就会搬到睡觉的房里,我利索的钻进被烘笼子烤得热乎乎的被窝,外婆继续纺纱。昏暗的煤油灯把外婆一摇一晃的巨大的身影映在板壁上,纺车有节奏的嗡~嗡~嗡~声就像无字的催眠曲,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儿时的记忆中,女人们一年到头似乎有纳不完的鞋底纺不完的纱线,后来才知道,一家老小脚上身上穿的床上铺的盖的,都出自于女人们不曾停歇的双手。尽管男人们几乎一年到头打赤脚穿草鞋光膀子,只有走亲戚才装装门面,小孩子过年时才能穿新衣服新鞋子,毕竟人口多供不应求。如果城里亲戚给小孩送了新鞋子,必定会宝贝似的压在箱底,走亲戚才会拿出来,光脚走几十里山路快到亲戚家时从腰间把新鞋解下来穿上昂首阔步进门。

主办单位:亚新综合体育·(中国)官方网站 网站运营:北京中电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400-007-1585
项目合作:400-007-1585 投稿:63413737 传真:010-58689040 投稿邮箱:yaoguisheng@chinapower.com.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编号:京ICP证140522号 京ICP备14013100号 京公安备11010602010147号